離開樂視的五年,我帶著傷疤生活

來源:首席人物觀(ID:sxrenwuguan) 作者:未未 編輯:江岳
2021年12月,樂視宣布了全員漲薪,等到月底,樂視視頻的 Logo下又新添了一句話:關鍵控好資金鏈。
如同一場黑色幽默。毫無疑問,它影射的是五年前。崩于資金鏈的樂視,付出了老板“跑路”和裁員70%的代價。當年夏天,北京上空飄滿了樂視的簡歷。
五年后,樂視的故事已經無人問津,震蕩的中心轉移到了后廠村。互聯網下行周期的霧霾籠罩在這里的每一條街道——在剛剛過去的2021年,阿里、騰訊、字節跳動、快手、愛奇藝、滴滴以及他們背后更多中小廠,都先后傳出了裁員的消息。
這些被裁掉的互聯網人,他們對于大眾的最后意義,似乎就是以突然的離開,證明互聯網的殘酷真相。他們留下了情緒,留下了話題,除此之外,無人真正關心他們的去向。
某種意義上,他們只是重走了一遍前樂視人的老路。
我們找到了樂視裁員潮中的小夢。五年前她收到的唯一賠償是一部黑色樂視手機,這還是領導自掏腰包給買的。物質損失并非全部,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推入更深的隧道——無法信任公司制度、社交焦慮、逃離互聯網信息、以及不論在哪工作,都會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。
當曾經堅固的世界風消云散,昔日的“螺絲釘”們該如何構建新世界?她至今還在找答案。
以下是她的自述——
螺絲釘
“我不知道樂視的資金鏈是怎么斷掉的,我也不知道賈躍亭是不是個騙子,他回不回國我更不知道了,這么宏觀的問題我回答不了,我當時只是里邊的一個螺絲釘而已哈哈哈。”
這是我離開樂視的第5年。當新認識的朋友得知我在樂視工作過,不等對方提問,我就會“官宣”這番聲明。
這是被太多人問過之后的條件反射。
現在我已經可以心態平和地說,“哎呀我當時就是一個小設計,公司層面的事兒,我還都是從媒體知道的。” 但在剛剛離職的第一年,被人問到時我總是很憤怒,甚至還和一位同學絕交了,因為他總是轉發一些樂視的負面新聞給我,還配上幾句自己的評論。在第四次的時候,我翻了個白眼,刪了他的微信。
我當時確實很煩躁。
很大程度是因為,我居然在離開時才發現自己的無知。雖然在樂視工作了一年半,但我似乎對這家公司的情況一無所知,甚至一直到2016年出現“裁員潮”的時候,我還堅信那是競爭對手派來“黑”我們的。畢竟,當年2月,我們剛剛在五棵松開過一場極有“排面兒”的“演唱會”,那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參加過最“燒錢”的年會。
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。活動當天,大家都無心工作,忙著討論幾點出發、各自位置、散場后如何再組織部門活動。所有人都很興奮。

五棵松體育館是2008年奧運會新建場館之一,但樂視在2016年1月冠名了它,改為“樂視體育生態中心”。在這樣的場館里開一場年會,這對于任何一家私營企業來說都意義重大。
2月28日下午,我們早早從樂視大廈出發,來到體育館。走進館內,一抬頭,我就看到了“樂視生態”幾個大字,旁邊還擺放著醒目的樂視Logo。
作為螺絲釘,我與有榮焉。
那晚的節目很多,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還是賈老板的獻唱。“吹啊吹啊我的驕傲放縱,吹啊吹啊吹不毀我純凈花園”,當賈老板唱到高潮時,全場的氛圍也達到了頂點,掌聲、伴唱和歡呼聲,交雜的聲浪從圍繞著舞臺的觀眾席上涌起,所有人都舉起手里的熒光棒晃動配合。

我也趕緊拿出手機拍照,配文:“年會。”一起上傳到了朋友圈,當然,發布的時候沒有忘記附帶一下五棵松的定位。
那條朋友圈很快就收獲了數十個點贊和評論。而當時,我的微信好友還不到300人。
一切的驕傲放縱,盡在不言中,毫不夸張地說,樂視當時就是我心里的純凈花園。那時的我不會想到,這條朋友圈會在不久之后被我鎖上,樂視會因為缺錢,提前終止與五棵松的合作。
而我這顆螺絲釘,也會被甩進命運的漩渦。
信任
我當時所在的部門,是樂視某子公司的品牌部。
相比其他部門的同事,我對公司品牌的信任感更強。后來我看到大家開始討論互聯網大廠的“內卷”,特別有感觸。很多自發的內卷其實是建立在對公司的信任之上的,是公司提供了足夠的安全感,讓身在其中的人相信:只要足夠努力卷,就會有足夠好的回報。
我當初就是對樂視生態的堅固充滿了信心,迷之信心。
這些信心,是被無數觸手可及的細節堆積出來的。比如,在東四環樂視大廈的正門前,印有彩色樂視logo的旗幟圍繞著紅色的五星紅旗飄揚在空中;跟我共事的同事里,很多都來自 BAT,他們都是因為看好樂視發展跳槽來的。

薪水自然是信心最結實的基礎。我跳槽到樂視,薪水接近翻倍,以前的同事和朋友知道我的新工作后,都會夸張地道賀,這讓我更加堅信,公司的實力足夠打造賈老板口中的生態。
每一個細節似乎都在暗示著“明天會更好”,也讓人愿意“敬業”。只要順著這個體系生存,就可以生活得很好。這是我們這樣沒有背景的年輕人,能改變境遇的最靠譜方式。
我確實也很努力。
按照規定,我們有一個半小時的午休時間。吃完午飯,我偶爾會跟同事一起在樓下散步,但會時刻關注著手機,查看微信群里的需求。
“這個項目是臨時決定上線的,你這邊能不能優先做一下?”作為設計,我經常接到這樣臨時插入的需求。這就像一道詔令,不管我當時在哪里,都會馬上趕回工位干活兒。不能因為我的效率影響了整個項目上線,這是我對敬業的基本理解。
我的同事們也大抵如此。大家身上也有這股勁兒。大廠的空氣里,似乎充盈著隨時觸發緊迫感的魔力。我很快形成了隨時在線的習慣。每天早晨被鬧鐘叫醒后,我的第一件事不是關掉鬧鈴,而是看工作群里的新消息,再去公司內部郵箱里轉一圈,看看有沒有新的通知。
在這期間,鬧鐘就在一邊叮叮咚咚繼續響著,不悅耳的鈴音提醒著我時間正在一點點流逝,連帶著閱讀和回復的速度也被加快了。
2016年11月,我收到了賈老板的那封內部全員信,他對公司的快速擴張進行了反思,并表示自愿永遠只領取公司1元年薪。我被打動了。我和不少同事還在堅信,波動只是暫時的,困難很快就會過去。
那封信發出去不久,還有離開的同事跟我聊,想等時機合適再回來。然而,情況開始急轉直下,2017年春天,公司門口開始出現了舉著橫幅討債的供應商,更大的“風波”接踵而至。我們每天上班都要在討債人憤怒的注視下開始,壓抑和恐懼,逐漸侵蝕了曾經牢固的信任。
5月,我和幾位同事向部門領導提出了離職。
領導讓我們等一等,他上樓去“堵”我們所在分公司的老板。這位老板是在“裁員潮”爆出后才剛剛上任的。到了這個時候,老板都是躲著我們走——擔心我們提離職和賠償。
當天晚上,我們坐在各自的工位上等消息。有人提議,不如一起來把王者榮耀吧。在共事一年多后,我們聚在一起打了第一把5V5游戲。等手機打到沒電,領導帶著老板出現了。“樂視正在最困難的時間,所有的生產線都已經停工了,但希望品牌部的大家可以多留一段時間,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各位在輿論環境下的努力。”
從未謀面的新老板,在空蕩蕩的辦公樓里對我們發出懇求,不久前,這里還坐滿了加班的同事。
自由
2017年6月,我正式離職了。裁員潮最后席卷到了品牌部。離開的那一天,我沒有拿到N+1,甚至連當月的工資都沒有如數結算。一臺黑色樂視手機,是對我過去一年半的唯一補償。
我堅持沒有使用那部手機,把它放回了老家平頂山,后來姐姐手機壞了,在新手機到貨前,暫時使用了一段時間。半個月后,它正式退休。至于和公司簽好的賠償協議,至今沒有兌換。

離開樂視后,我有大概一年的時間沒有上班。
需求沒了、周報沒了、就連不定期的全員郵件都沒有了,大段的時間被空出,某種意義上,我獲得了畢業后難得的自由,唯一保留下來的,就是時刻回復信息的習慣。當時我天天躺在床上打王者榮耀,但在回血的幾秒鐘內,我會快速切回微信,看看有沒有人來找我。
不過,對于大部分信息,我都選擇不回復。有一次,一個朋友從武漢來北京,來之前給我發微信約見面。我看到那條微信后,繼續切回了王者榮耀。
我不是討厭他,只是單純的,喪失了與人交流的興趣。準確地說,我對外界一切都喪失了興趣。
我被孤獨包圍了。
法國現代派詩人波德萊爾曾描寫過大街上的現代主義:“我急沖沖地穿過林蔭大道,縱身跳過泥濘,要在這一團混亂的車流中避開從四面八方奔騰而來的死神。”這段描寫后來被美國作家馬歇爾·伯曼引用進了自己的新書《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》中。
在伯曼看來,被拋入車流中的行人,與快速發展的現代都市在進行著孤獨的抗爭——從樂視離開的很長時間里,我都陷在這種孤獨的抗爭里。
我不想繼續在北京找工作,樂視的這段經歷讓我對工作失去了安全感,“樂視都這樣了,我還能去哪呢?”大部分時間,我就躺在家里,平均一周打開招聘軟件,象征性地看一眼。
這樣的日子持續了10個月后,我決定回家。
我退掉了北京的房子,收拾行李,回到老家平頂山,想找家培訓機構當美術老師。但我很快發現,老家沒有我想要的自由。面試我的老板繪畫水平還不如我。當他給我開出月薪1000元和不交五險一金的待遇時,我覺得我們沒了再談下去的必要。

再次離開家的導火索,是鄰居和我媽的一次對話。
“她該不會在北京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出問題了吧,染了一頭灰毛回來,也不上班,打算靠你養嗎?”鄰居在客廳壓低聲音問,我媽也壓低了聲音回答:“反正也管不了,湊乎過吧。”
31歲、未婚、失業,這在河南的小城市,的確是典型的反面教材。我在高三那年就離開了平頂山跑到北京學畫畫,那時我19歲。之后,我在北京上大學、工作。“北漂”十年,我就是為了回家給別人當“反面教材”的嗎?
就這樣,我重新回到了北京。那是2019年5月,我在最短時間內,入職了一家制造業公司。
公司不大,選擇那家公司是因為我覺得面試官(也是我后來的領導)人很好。面試結束后,她親自帶著去樓上找hr,進行第二輪面試,又在我面試完準備回家的時候,告訴我哪條路容易堵車,我怎么回家會比較方便。
進樂視前,我看重平臺,現在我更在意職場環境。
夢醒
不過,在制造業的那份工作,我還是只堅持了4個月。因為我的工作內容不只是設計,還要跟合作方對接,到后來,我甚至還要寫文案。

雜亂的工作內容和不明確的考核標準,讓我很難像過去一樣梳理自己的業績。我的恐慌和焦慮再次被激發。
辦離職的那天,領導還是和第一天面試那樣,送我進電梯。“公司在發展到不同階段的時候,會有不同的需求,你趁這段時間可以先想一想自己的需求。”
我的需求是什么?更高的薪水、更大的平臺又或者是更好的業績,這些職場里的誘人條件,對我來說,都比不上一個更有安全感的地方。哪怕這份安全感只是因為有熟人在,可以讓我從“孤獨地抗爭”中,短暫地解脫出來。
我最后選擇了朋友開的一家小創業公司,主要為品牌方提供內容創意和制作,團隊人不多,氣氛也很寬松。
接到朋友邀請時,我剛剛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offer。朋友這邊能提供的薪水低很多,但有兩點實在太吸引我:簡單,沒有亂七八糟的事情;做完本職工作還可以在辦公室忙自己的私活。
其實離開樂視后,我一直有做自由職業的想法,朋友的offer,也相當于半自由職業。
“樂視都倒了,沒有什么公司值得信任,還不如去和熟悉的人工作。”后來我就這樣向周圍人解釋自己為什么會降薪來到一家小公司打工。
在由人情構成的工作室里,確實更加自由。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去工作,中午到公司后,先在公司里慢慢悠悠煮個湯,一邊盛湯一邊問茶水間外的人:“有誰要喝湯,今天煮的是銀耳雪梨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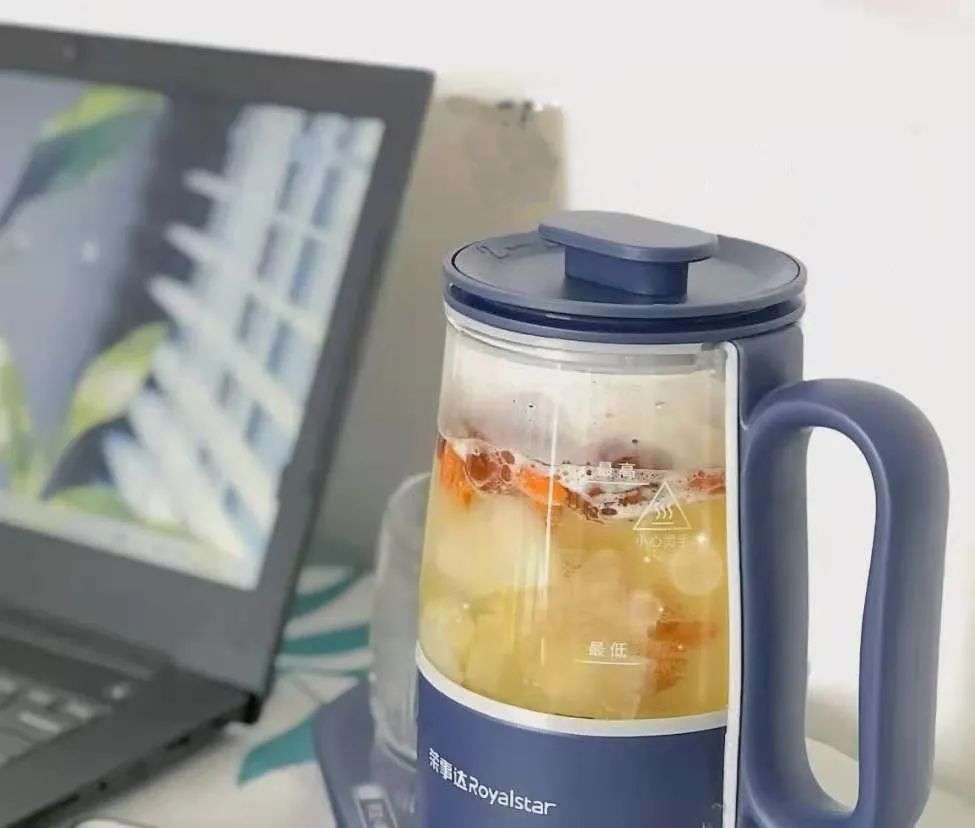
等大家一起喝完湯,我們再開始工作,晚上忙完就可以回家。老板還很愛放假,年假向來是半個月起步,不過項目忙起來的時候,我也得睡在公司。
要說這份工作對我最大的挑戰,大概是適應從甲方到乙方的轉變。
某天深夜,一位同事突然給我打電話:“快去領紅包,甲方在群里發紅包了,記得表達感謝。”我領到了1.22元的紅包,同時獻上了一連串“謝謝老板”的表情包。
不過在這里,我確實被修復了。大廠螺絲釘的快樂和痛苦,都離我遠去。
2021年的最后一天,我收到了樂視前同事的微信:要不要一起出來吃烤肉?離職后的一年,我除了窩在家里打游戲,就是和他們一起呆著。五年時間,我們見證彼此的難過與成長。
我赴約了。當晚一起吃烤肉的有4個人。除了我之外,其他三個人,一個在廣東開民宿、一個考公上岸,進了體制,只有一個人,去了另外一家互聯網公司。
從物質上,最后那位選擇了互聯網公司的朋友拿到了更好的報酬,而其他人在離開樂視后,收入和平臺都在“掉落”。但經歷并走出樂視之痛,我們對自己想要什么,都有了新的理解。
比如,在我看來,自由比成功更重要。安全感離不開金錢,但也不能完全靠金錢。而真正的安全感,與物質無關,它是內心的一種狀態。
12月的時候,樂視漲薪的新聞傳出,作為現任老板的朋友問我:“你會不會再回去呀?”我回頭白他一眼:“當然不回去。”“但我也可以隨時離開你。”后半句話我沒有說出口。
很難說這是好習慣還是壞習慣,但做好隨時離開的準備,是我在離開樂視以后學會的第一件事。
圖片來源于網絡,侵刪









